(1)
1925年夏季的一天,一场瓢泼大雨笼罩了北京城郊。雨中的永定河陡然变得暴躁起来,它“吼吼”地咆哮着,卷着从上游带下来的泥沙、杂物,从三家店方向向东倾泻下来,浑黄的浊浪蛮不讲理地撞击着卢沟桥下的“斩龙剑”,但很快就被“斩”成了朵朵浪花,随后马上又重新汇入浑黄的激流中,气势汹汹地闯过卢沟桥下的桥洞,闹哄哄地向下游奔去……
眼前的西山,被雨幕笼罩得朦朦胧胧,看上去透着几分神秘,仿佛变成了传说中的神仙境地。京汉铁路上行进着的列车,在雨幕中看上去仿佛成了漂泊在水面上的船,随着雨幕的变化,就好像已经“漂”了起来。厚厚的雨幕将天地连接在一块儿,“刷”地一道利闪过后,接着便是惊天地动的一阵雷鸣。顷刻间,大地仿佛都被雷声震的晃动起来,那巨大的雷声在天地间回荡着,久久不能平静……
这雨下了溜溜儿的一天,快到黄昏时才住了。大雨消去了天地间的酷暑,人们顿觉凉风习习,空气也显得格外清新,给久受天地间“蒸”、“焖”、“烤”的人们,带来了难得的惬意。被大雨洗过的天空,变得湛蓝湛蓝的;一道彩虹挂在天边,更增添了大自然的绚丽多姿。河边儿的草丛中,成群的青蛙亮开嗓子唱了起来。经过雨水的冲刷,就连卢沟桥上的石狮子也变得神气起来,看上去透着格外精神。
离卢沟桥不过二三里地的沿河镇大街上,一个身材高大、秃头、光着膀子、身上刺着青龙的黑大汉,带着一群打手,一路上咋咋呼呼、骂骂咧咧地自南向北行进着。黑大汉一边走一边扯开嗓子高声吆喝道:“老少爷们儿听喳,俺是沧州的刘黑塔,今天来到沿河镇,就是要把‘小白龙儿’拆巴了,让他狗操的尝尝俺的厉害。老少爷们儿都来看哪——”
大汉身后的十来个打手,也亮开叫驴般的大嗓门儿,喳喳呼呼地口吐狂言。
见没人搭理他,领头儿的大汉觉得有点儿不过瘾,便侧过脸来,自己给自己搭了个“台阶儿”,对身边的喽啰说道:“等会儿那小白龙儿要是见了俺,你说他……,他会怎么样?”
“还用见着您吗?那小白龙一听说黑爷您来了,准他娘的比兔子跑的还快;早他妈跑得没影儿啦!”
旁边儿的另一个打手,忙凑上来说着便宜话:“他还跑得了吗?我猜他一听说黑爷您到了,准他妈立刻就吓得尿了裤子,当下就得瘫了……”
众人放肆地大笑起来。
黑大汉卖弄地把一块砖高高抛起,然后接在手上,大吼了一声,同时使劲儿朝自己发亮的光头上砸去。那块砖立刻碎成了若干小块儿,四周立刻就响起了一片喝彩声。那黑大汉更来劲了,喷着老高的吐沫星子,瞪大了眼珠子,头上的青筋暴涨,高声叫着、骂着,在一伙打手的簇拥下,继续朝前走去。
这些年来,沿河镇铁路工厂里保定帮和沧州帮的工人,毫无原则且没完没了地打冤家。大规模的械斗就发生过十来起了,双方都有人被打得腿折、胳膊断的,也都有人被警察抓去蹲了班房。双方的仇恨越结越深,摩擦一直不断。今天这位体壮如牛的黑大汉,就是沧州帮最近专门花钱从沧州老家请来的打手,专门儿来沿河镇对付保定帮在龙王庙门前摆跤场的李谦、王万成这对表兄弟的。自打李、王表兄弟二人在沿河镇北关外摆跤场子以来,小半年儿了,还没遇到过对手。保定帮的人因此自然挣足了面子,沧州帮的人当然不能容忍!今儿个就得见见“真章儿”,论个高低;分出个胜败输赢来。了解内情的人放出话来:今儿个可是一场“玩儿命”的较量,弄不好就得出人命啊!
保定地面儿一直是住兵的地界儿,那些从队伍上被淘汰下来的大兵,没别的谋生技能,就把自己的一身武艺当成了混饭吃的资本。退役的大兵们,或者去拳坊、跤场当专门儿教那些富家子弟学“把式”的教师爷,或自己开设武馆、跤场,带徒传艺。日子长了,保定府的练家子,特别是跤手,在京、津两地甚至山东、关外渐渐就有了名气,以致江湖上传出这样的顺口溜:“京油子、卫嘴子、保定府的勾腿子。”所谓“勾腿子”,就是市井百姓对跤手的一种略带调侃的戏称。京、津、保等大城市里,居然有了专以“表演撂跤”为业的“把式”;刨根儿问底儿一打听,这些跤手十有八九都是保定人。
据史籍载,沧州民间武术,兴于明,盛于清,至清乾隆年间,沧州的武术之乡格局已形成;至清末,则声扬海外。自古燕国至明清,多代王朝建都于幽燕,沧州乃畿辅重地,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据史籍记载:自齐桓公二十二年(前664)齐桓公援燕山戎以来,各朝各代均有多次战争发生于沧州一带。频繁之战事,民遭涂炭,民生维艰,故须掌握攻防格斗之技方能自救图存。沧州,古有"远恶郡州"之称,明时有"小梁山"之号,可见沧州武风之盛和武术之发展,与特定地理环境关系甚密。
两地都是“武术之乡”,都是出“英雄豪杰”的地界儿;但两地谁为“最”,就成了无解的难题。人守家在地时好说,一旦出门儿在外,人们就变得极为敏感。在家门口儿时,一旦与人发生冲突,人们大都采取“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”的做法。可一旦出门儿在外,人们就会受那句“物离乡贵,人离乡贱”民谚的影响,与别人稍有“碰撞”,就会理解为“受了别人的欺负”,经常会为很小的一件儿小事儿而“拔剑而起,挺身而斗”。在沿河镇谋生的保定、沧州人的矛盾,说到底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引起的。可人们的仇恨却在日益加深,械斗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频繁。今儿个这个沧州黑大汉的出现,肯定又得惹出乱子来。
没有不透风的篱笆,沧州帮的人从老家请来了高手,要来砸象征着保定人的荣誉的跤场;很快就在铁道以西的铁路工厂保定人居住的窝棚区传开了。保定帮的老大、铁路工厂木工场的大工匠李四儿,站在土坡上,双手做成喇叭状,向那些高矮不等的窝棚大声吆喝着:“保定帮的爷们儿听喳,沧州帮又来砸咱们的场子啦,大伙儿快跟我去跟他们较较‘真章儿’,谁他妈也不许当孬种!”不一会儿,李四儿身边就聚集了几十口子手持棍棒的工人。李四儿把手一挥,领着大伙儿朝铁道东的跤场走去。
此刻,在龙王庙跤场前,沧州帮的打手们推开众人,拥着刘黑塔走进了场内。四周围观的人们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,紧张地打量着这位浑身煞气的黑大汉。
号称“小白龙”的跤场场主的李谦,此刻却显得非常沉着。他明白:这准是沧州帮又请来了什么高人,来砸跤场了。这场面他见的多了,所以他并不特别紧张,他轻轻吹着茶碗里飘浮着的茶叶,静等着对方开口。他知道:凡是拿了人家的钱,帮人家到某处“拔份”的主儿,绝不是什么真正的武林高手。
刘黑塔双手交叉抱在胸前,厉声吼道:“谁是小白龙儿?大爷我要会会他。”
小白龙刚要站起来,他的表弟王万成,忙从背后按住了他的肩膀,小声说:“表哥,还轮不上你出场呢,瞧我的。”说罢,王万成迎上前去,冲刘黑塔一抱拳,板起脸来大声说:“这位朋友,你……有什么事儿?”
刘黑塔一边往前凑,一边喷着老高的吐沫星子吼道:“老子想吃龙肉了。”说罢便扑了上来。
王万成忙伸手接住了刘黑塔,二人在场上撕掳起来……
就在这时候,保定帮的老大,铁路工厂木工场的大工匠李四儿带人赶到了。围在外面的人们忙给李四儿让开了一条道,李四儿带人走进了场内。与此同时,沧州帮工头儿徐天亮也带着一群人,从另一侧挤到了场子里。场上撕掳在一起的俩人见状立刻停止了争斗。
李四儿用轻蔑的眼神打量了一下刘黑塔,冷笑了一声说道:“听说你们沧州也是出好汉的地界儿,你小子怎么一点儿规矩都不懂,上来就动手撒野呢?”李四儿早年在保定老家闹过义和团,为此还蹲过官府的大狱,是个见过世面的主儿。他是当年应聘铁路工厂为慈禧和光绪皇上建造“龙车”,才来到铁路工厂的。靠着精湛的木工手艺,李四儿现今已经是铁路工厂木工场的大总管了,全厂数得着的“大工匠”。
刘黑塔身后走出沧州帮的工头儿徐天亮,上前冲李四儿一抱拳,冷笑了一声接着说道:“四……哥,李四爷;俺们这么做,这都是你们逼的!”
李四儿冷笑了一声,不快地说:“徐师父,俺们保定府的人好摔跤,摆个场子自己练着玩儿,碍着你们什么事儿啦?”
徐天亮用手一指跤场上悬挂着的杏黄色的横幅,不满地说:“四哥,你看看你那横幅上写的字儿,太欺负人了吧?啥叫‘天下无双’?你大概都找不着‘北’了吧?我看这沿河镇都搁不下你了吧?”
李四儿笑了笑,板起脸来说道:“徐老弟是不是连咱们直隶地面儿上的俗语都忘了?人常说,‘京油子、卫嘴子、保定府的勾腿子’。俺保定府自古就专门出摔跤的好手儿,讲究伸手不留情,抬腿见输赢;这……就是‘天下无双’啊!”
徐天亮顿时脸色煞白,把脚一跺,大声说道:“俺就是不服气!什么‘勾腿子’?俺听说是‘狗腿子’。那话的意思是说,你们保定人天生就会给人家当奴才……”
李四儿涨红了脸,狠狠地一跺脚,用手指着徐天亮大声吼道:“你放屁!”说着话,李四儿摞胳膊、挽袖子,就朝许天亮跟前凑。双方的打手们也骚动起来,人越聚越多,人群涌动着,乱成了一片。眼看着双方就要动手啦!就在这时,沿河镇的警察署长马剑飞,骑着马,带着一队警察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了龙王庙前。到了跟前儿,马署长一勒马缰绳,那马“咴咴”地叫着,两条前腿儿一下子立了起来;在地上转了一圈儿,这才立住了。马剑飞用马鞭子的鞭杆儿支了下已经耷拉下来的大盖帽,操着河南口音大声吼道:“住手!恁这伙兔孙快他娘的住手——”
跟马署长一起赶来的警察冲进了场子上,也都扯开嗓子大声吆喝着,故意把大枪的枪栓拉得发出响声,很快把控制住了局面,躁动的人们立刻就安静下来。
工头儿李四儿走到警官跟前,换了一副笑脸,冲着马上的警官一拱手,大声说:“马署长,你得给俺们做主。俺们在这儿开跤场,可是在警察署备了案的。今天徐天亮带人来捣乱,无缘无故地找茬儿打架,这分明是欺负俺们保定人老实呀!”
徐天亮赶忙上前分辨道:“马署长,您可都看见了,他们跤场的横幅上竟敢写着天下无双,啥是‘无双’?那就是第一呀!您说这……”
马剑飞麻利儿地跳下马来,把马鞭子背在身后,仰起脸来冷笑了一声说道:“二位,我可提醒恁俩:恁两家欠人家寿仙堂药铺郝大夫的医药费,啥时候去结清了呀?我要是再晚来一步,今儿个又得伤几十口子;末了儿还不是得让人家寿仙堂的郝大夫白给恁们治伤看病?恁们是吃准郝大夫好心眼儿了,拿不出钱来,郝大夫照样儿给恁的徒弟治伤看病是吧?徒弟……没钱,恁俩当师傅的可是大——工——匠!恁俩也他娘的没钱吗?每次到寿仙堂去给徒弟们治伤,恁俩有钱的师傅为啥不肯出医药费?要脸不?都是他娘的卖苦力的穷工人,成天打啥架?你说保定人厉害,他说沧州人英雄;我看都是他娘的扯淡!老子自小进少林寺学武,后来又跟着冯玉祥冯老总打了五六年的仗,这么办吧,恁们谁敢跟俺比试比试?要是赢了我,就算恁厉害,咋样?”
李、徐二人都咽了口唾液,胆怯地低下了头。
马剑飞又用手上的马鞭一指跤场上的横幅,板起脸、瞪大了眼珠子对李四儿说:“你他娘的马上把它给我摘下来!俺冯老总都没敢说他‘天下无双’,你们他娘的算老几,也敢吹恁自己‘天下无双’?”
李四儿极不情愿地点了下头,转过身儿对手下人吩咐道:“听马署长的,把那横幅摘了!”
马剑飞又冲那黑大汉一招手,接着吼道:“你小子是哪儿来的?到俺沿河镇来干啥?”
工头儿徐天亮忙陪着笑脸对马署长说道:“马署长,这是俺从沧州老家请来的教师爷,专门教俺的徒弟们学功夫的。嘿……”
马署长怒气不休地说:“光天化日之下,你个兔孙当着沿河镇大街上恁多的大姑娘、小媳妇的面儿,光着个膀子招摇过市;你他娘的像啥?咋?我听说你还在大街上拿砖头往恁那头上砸?那你试试俺的枪子儿呗?”说着话,马署长掏出手枪,顶住了刘黑塔的头。刘黑塔竟然吓得尿了裤子……
徐天亮忙冲马署长连连作揖,低声下气地央求道:“马署长,不能啊!俺可知道,无论啥‘金钟罩’、‘铁布衫’,可都挡不住枪子啊!”
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马剑飞收起了手枪,生气地接着说道:“我最见不得这号臭流氓!到了俺的跟前,就得好好治一治这些臭毛病!”
黑大汉颇不服气地说:“长官,俺这是‘以武会友’哇!他们敢公开摆场子,那可就挡不住有人来访;这是江湖上的规矩。俺今天到沿河镇来,就是想跟那‘小白龙’比试比试。俺要是输了,就跪下给他磕头,随后立马就滚蛋;这辈子保证不再来沿河镇地面儿。他要是不敢,那就是亚细亚的火油——虎牌儿的!狗掀帘子——嘴上的能耐。俺这是以武会友……”
马署长一瞪眼,大声说:“有恁这么‘会’的吗?一上场就骂骂咧咧、口吐狂言,还当街拿砖头往自己头上砸,你混蛋——”
黑大汉连连后退,低下头小声说:“是,长官,俺……有错儿。可俺今天既然来了,就得和‘小白龙儿’过过手。还求马长官您成全!”
马署长想了想,随后点了点头,说道:“行啊!以武会友……俺懂。那你得……客客气气地先给人家作揖行礼,跟人家说‘请多指教’,还得人家愿意;恁俩人才能交手。各行有各行的规矩,跤场上的规矩……你懂吗?”
黑大汉忙说:“俺懂。点到为止,不能伤人。双方得穿上跤衣、靴子才能交手,不能使用反关节动作,也不能造成直接造成对方肢体疼痛,三点着地即为输……”
马剑飞笑着说:“行啊,看来你小子还真不是外行。”
他又把脸转向小白龙儿,低声问道:“李谦,这个兔孙说今儿个来‘会’你的,你……愿意跟这小子过手吗?”
小白龙儿赶紧一抱拳,大声说:“俺愿意!”
马署长哈哈一笑说道:“给俺搬把椅子来,听说‘小白龙儿’自打来沿河镇摆场子,还从没输过?那一定是好功夫!恁俩交手肯定是一场好戏!来,让俺也开开眼……”话音未落,有人真的给马署长搬来了椅子,还有人给马署长递上了热茶。
李谦在徒弟们的帮助下,忙穿上跤衣,登上靴子,走到场上,飞身拧了个旋子,转身又来了个二踢脚,然后冲黑大汉一抱拳,大声说:“请!朋友请——”
黑大汉在助手的帮助下,忙穿上跤衣、靴子,随后活动了几下腰腿,便挥舞着双手,跳着车轮步,冲李谦扑了上来。原本喧嚣的跤场上,立时就安静下来。李谦抖擞精神,和刘黑塔搅在了一处……
这时,在龙王庙不远处的大道上,两挂大车自卢沟桥方向驶来。前边的车上装着一口黑漆棺材,后边的大车上罩着芦席搭成的棚顶,看来那辆车是专门儿坐人的。一位50开外的老爷子跨在后边那辆大车的车辕上,几个青壮年男子紧随其后;看样子,这两辆大车是专门儿运送灵柩还乡的。当时不兴火葬,交通又不方便,人死在外乡,总要想方设法把死者的尸首运回老家去安葬。所以,当时的丧家都讲究雇一辆大车,把死者的灵柩往家里运。沿河镇是北京通往中原各省的必经之路,常能见到这种运送灵柩还乡的大车。
两辆大车一进沿河镇北关,就见龙王庙前看热闹的人围了个里三层、外三层,人群中还不时爆发出阵阵喝彩声。跟车的几个小伙子觉得好奇,刚要往上凑,那位老爷子便喝住了他们:“给我站住!有啥好看的?没见过打把式卖艺的?讨厌……”
几个年轻人无奈地笑笑,只得跟着大车,继续往镇子里走。
沿河镇的五里长街,十分繁华热闹。路旁摆摊儿卖西瓜的小贩扯着嗓子,大声吆喝着。临街的饭馆儿里,不时传来跑堂的伙计报菜名儿的吆喝声。一棵大槐树下,用白布支起的说书棚内,随着一阵悠扬的三弦、四胡的伴奏声,一个姑娘正在用悦耳的京腔,唱着京韵大鼓:“二八的那个俏佳人儿,懒……梳……装……,崔莺莺哟得了这么点病啊,是躺在牙床。躺在了床上,她是半斜半卧,您说这位姑娘,乜呆呆又(得儿)闷悠悠,茶不思、饭不想、孤孤单单、冷冷清清、困困劳劳、凄凄凉凉、独自一个人、闷坐香闺、低头不语、默默不言、腰儿受损仔,乜斜着她的杏眼,手儿托着她的腮帮……”掌声、怪声怪调的喝彩声骤起,顿时就淹没了大鼓妞儿的歌唱声。
旁边儿的赌场上,赌棍们正大声吵吵着,往桌儿上押着钱。
一栋小楼前,门口儿挂着一块匾,上书“翠花班”三个字。楼上传来阵阵淫荡的歌唱声和男女打情骂俏的声音,门口儿还站着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,嘴里磕着瓜子儿,用猎人般的眼神在过往的行人中搜寻着,并不时扬起右手握着的手帕,放肆地向门口儿的行人招呼着:“相好的,快来呀……”
押车的老人回过头,对弟子们低声吩咐道:“你们几个听好了,谁要是敢去找野娘们儿,回头我就把他狗日的腿打断!看什么?快走——”
“是——”几个年轻人吐了下舌头,赶忙低下头,跟在两挂大车后边,急匆匆从“翠花班”门前走了过去。
一个手持牛棒骨的叫花子,正在一家饭馆儿门口儿边敲边唱着:“掌柜的,你别发火;如今已然是民国,前清的时候我要饭,如今要饭的还是我……”
老者忙跳下大车,挥舞着手里的鞭子,小心翼翼地赶着大车朝前走着。他脸上挂着谦和的微笑,操着地道的“京腔儿”吆喝道:“借光、借光喽!劳您驾,您让让;谢谢、谢谢喽……”大车缓缓地穿过街道,来到了一家挂有“山西会馆”的牌子的客栈门前。老爷子吆喝住了牲口,停了下来。门口儿的伙计的赶紧迎了出来,操着山西晋中的口音笑着说:“客官,住下啵?”
老者恢复了浓重的山西口音说道:“啊,是;就住你这儿吧。”
伙计眼一亮,欣喜地说:“听口音,你们是咱山西老乡?山西哪个地界儿的?”
老者操着山西口音笑着答道:“我们是太原府的。”
伙计的忙把脸转向了身后的院子里,拉了个长音儿,用软绵的山西口音招呼着里边的伙计:“来——客——啦,里边儿的,赶紧伺候喳——”
话音一落,两个伙计打开了跨院儿的大门,帮着把两挂大车赶了进去,接着又麻利儿地帮着卸了大车上的牲口套,把拉车的六匹骡马牵到了槽头,麻利儿地添上了草料。
刚才在门口儿兜揽生意的伙计显然是个“大伙计”,他低首垂眉、恭恭敬敬地对几位客人说:“几位爷是住平房,还是……”
“不,我们不住平房,我们住楼上。”
为首的那位50多岁的长者抢着搭了话。大伙计连忙笑着把几位客人从跨院儿的月亮门儿带到了正院,让到了楼上的房间里。
开饭馆儿、旅店的人眼界子宽,客人一上门,只需三言两语,就能把对方的身份摸个八九不离十。这几位客人往客房桌儿旁的椅子上一坐,大伙计便看出:这几位可不是普通的客人。搭眼看上去,这几位无疑是那年月常有的运死者的灵柩还乡的。可这几位当中,却没有一位戴孝的,这便有点儿不合常理。当初若没有本家直系亲属在场,谁敢把死者放进棺材中?既然“入殓”时有亲人在场,送葬的人当中咋会没有戴孝的呢?再看这几位爷的走路架式,一个个全都是挺胸收腹,两脚全是“外八字儿”;他们坐下后,腰也全都挺着。甭问,这几位全是“练家儿”。
再一看这几位爷的打扮,衣服的面料虽然都是粗布,样式也全是手工缝制的中式衣服,可一个个的衣服都特别的干净;可见,这几位爷决不会是卖苦力的。大伙计当时眼珠儿一转,忙让小伙计麻利儿的从厨房端来四个冷荤、一壶酒。
那位长者用手一挡,笑着说:“酒……就免了,伙计,您给沏壶茶吧。”小伙计高声应着,放下手里的木托盘,又端起那壶酒,下楼去了。不一会儿,便拎着一只圆柱形的大茶壶和几个茶碗,二次来到了楼上。屋里的几个客人边喝着茶,边聊着刚才的这场雨;那位长者认真地说:“你们几个瞧见没有?刚才咱过卢沟桥时,桥下的水都浑了。”
“水浑了……说明什么呢?”一个徒弟问道。
长者微微一笑,抿了口茶,说道:“说明上游的雨还要大,把山上的泥土、石块儿都冲进河里了,河水这才变得浑浊了。这永定河还有个别名,就叫‘浑河’。”
大伙计听到这儿,不禁又抬头打量了一番这位长者。看来,这位是经常出入北京的客人;对这条道儿上的情况已经很熟悉了。大伙计赶忙下了楼,又命人端来几个热炒,随即便将一碗碗的山西馆子的传统吃食——刀削面端了上来。
小伙计刚要离去,那位老爷子又叫住了他:“伙计,老家是哪儿的?”
小伙计后退了一步,低首垂眉用地道的山西话笑着答道:“小地方,平遥的。”
长者微微一笑,接着说道:“我们明天回山西,你……可有什么东西要给家里捎的?”
“谢谢老掌柜,前天刚托人给家里捎了钱;不用麻烦您了。”
长者迟疑了一下,又问道:“跟你打听一下儿,从这儿往南走,道儿上……可太平?”
“回老掌柜的话,再往南走就是良乡县地界了。两县交界处……可不大好说,您还是多加小心。”
长者点了点头,长出了一口气,小声说:“知道了,明天早点儿叫醒我们,鸡叫两遍我们就上路。”
“是喽!”伙计应了一声,笑吟吟地退了出去。
夏夜,庭院里静悄悄的。月亮在云层中时隐时现,墙根儿处的草虫发出阵阵的呻吟,几棵参天古槐浓密的树叶儿摇曳着,把月光筛成小碎块儿,均匀地撒在青石板铺成的地面上。渐渐地,楼上、楼下客房里的灯逐渐都熄灭了,渐渐地从屋里不时传出粗细不等、轻重不同的鼾声。门房儿门口儿挂着的马灯还亮着,看门儿的胖老头儿一边掏着耳朵,一边哼哼唧唧地小声唱着山西梆子《打金枝》。
在跨院里,槽头上的骡马“呼喳呼喳”地吃着草料。各种大车在院子里一溜排开,把院子占得满满的。平房里的人们早就进入了梦乡,和楼里所不同的是,大通铺的平房里当中的柱子上悬挂着的马灯,通宵都亮着。这些卖苦力的、车把式们挤在大通铺上,睡得格外香甜。屋里弥漫着呛人的汗臭味儿、劣等得旱烟味儿;有几位的“呼噜”声,打得堪称是惊天动地,加上蚊子也放肆地叫着不断地向人们袭击,不是困坏了的人,在这环境里根本无法入睡。
楼上的大掌柜的尤鹏,摇着手上的白凌子折扇,来到楼上几位山西客人的房间,挑门帘走了进来,冲大伙儿一拱手,笑着说:“几位爷辛苦!”
老者忙起身还礼,仔细打量了这位尤掌柜的一番,笑着说道:“看样子,您是这儿的掌柜的吧?”
尤鹏笑着说:“老人家好眼力,在下尤鹏,正是这山西会馆的掌柜的。”
老人仔细打量着这位尤掌柜的:这位尤掌柜看上去大约四十多岁的年纪,多肉的脸上显得很松弛,眼泡也肿胀着,看上去总像还没睡醒似的。老者笑着说:“掌柜的……说话咋一点儿咱山西口音都没有哇?”
尤鹏笑着说:“我出来时间长了,这口音早就变得南腔北调的了。”
老者赶忙换成了地道的北京口音,说道:“掌柜的府上是……”
尤鹏赶忙答道:“小地方,嘿嘿;山西平遥张家堡的。”
老者微微一笑,眯起眼睛,又换成了山西口音说道:“我记得沿河镇山西会馆当年的掌柜的姓高哇!他是咱山西祁县人,请问,他和您……是啥关系?”
尤鹏紧张地干笑了两声,接着说道:“不错,原来咱这山西会馆的东家是姓高。后来,高东家被土匪绑了票,之后这买卖就做不下去了。高东家就把这所房产卖给了我,他就回了山西老家。沿河镇通了火车以后,商家大都改用铁路运送货物,驴驮马拉的商队没啦,保镖的镖局也混不下去了;连带着咱这旅店的买卖也一天不如一天。”尤鹏发现自己说跑了题,忙冲老者笑了笑,接着又说道:“请问老先生尊姓大名?您府上哪里?何处发财?”
老者迟疑了一下,极不情愿地说道:“在下高万祥,原籍山西洪洞人士,如今在太原开了个小买卖,哈……”山西的买卖人非常忌讳陌生人之间的相互盘问,萍水相逢,何必非要盘根问底呢?高老爷子脸上的不快显露出来。
尤鹏的眼睛一亮,重新打量了老者一番,满脸堆笑地拱手问道:“老先生莫非就是太原府大通镖局的掌门人,江湖上人称“通臂王”的高万祥高老侠吗?”
老者先是一愣,接着连连摆手,慌乱地说道:“不、不,我和大通镖局的高东家……只是同名而已。在下……是做药材生意的,从来不会舞刀弄枪的。我看尤掌柜的年纪也不小了,按说也该告老还乡了吧?”高老爷子反客为主,也拿话将对方一军。
尤鹏忙说道:“本想把这店房转手卖了就回山西养老,可连着两次直奉战争,搅得商人们都没心思做买卖了,这店铺也就卖不上好价钱了。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买主,也只好先这么硬撑着。好在我身体还行,家中老伴儿已经故去,儿孙们也都大了,这思乡之心也就不那么厉害了。请问高老先生,您运送的……是您的什么人哪?”
高万祥忙转过脸去,紧张地说:“那是我的账房先生,他在北京突然发病去世了。总不能把他的尸骨扔在外乡吧?我这才雇了辆大车,打算把他运回山西老家去。”
尤鹏微微一笑,说道:“高掌柜的,如今兵荒马乱的,道儿上……可不大太平啊!”
高万祥先是一愣,随即哈哈大笑起来,说道:“道儿上‘不太平’怕啥?咱还怕会有人抢棺材里装着的死尸吗?真要有人抢的话,倒也省得我千里迢迢地往山西运了。”
尤鹏只得跟着大笑起来,随后伸了个懒腰,赶紧起身告辞了。
尤掌柜的走后,高万祥忙招呼手下人,也上床睡了。
夜深了,不远处火车道上传来的火车的轰鸣声,此刻听来格外清晰。山西会馆里的更夫敲着梆子,在大院里巡视着。跨院儿简易的大通铺房间内,住店的客人有的发出惊天动地的鼾声,有的还说着梦话。牲口棚槽头上挂着的马灯,发出微弱的亮光。伙计一面哼哼唧唧地唱着山西梆子,一面用筛子往槽头上添着草料。
突然,房顶上出现了一个蒙面黑衣人,他伏在房顶上,小心翼翼地探出头,俩眼向院子里停放着的那辆装着棺材的大车死死地盯着。过了一会儿,他从房顶上掰下一小块儿瓦片儿,甩手向棺材上投去。
瓦片儿击在棺材盖儿上,发出“当”的一声响;声音并不大,但还是惊动了旁边儿那辆带蓬顶的大车里藏着的人。瓦片儿砸在棺材盖儿上后,立刻就从并排的带篷的大车上跳下两个手持单刀的人,他俩立刻在大车前列好了格斗的架势。
房顶上的蒙面人见状忙一缩头,躲到了房脊的另一侧,屏住呼吸,竖起耳朵,仔细地听着院子里的动静。
喂牲口的老头儿吓了一跳,忙对突然出现的二位持刀的客人紧张地说道:“二位爷……咋没回房歇着?”
持刀的客人没好气儿地说:“少废话,干你的活儿去!”
老头儿尴尬地笑了笑,忙喂完了牲口,快步转身走了。边走他还边嘀咕道:“棺材还用人看着?还怕谁偷死人不成?出门在外的人说话还那么横,你小子这是没吃过亏呀!”
房顶上的蒙面人消失了,再也没露面儿。两个持刀的人这才重新回到了带蓬顶的大车里,小院儿又恢复了宁静……
房顶上的蒙面人,像狸猫似的,很快就从房顶上来到了大掌柜的尤鹏居住的房间窗外。他轻轻敲打着窗棱,小声说:“掌柜的,我试探过了;棺材旁……确实有人守着。”
屋里传来尤鹏低沉的声音:“赶紧上山,召集弟兄们连夜下山,在沿河镇外独龙岗候着他们。记住,让他们把活儿干得利索点儿;千万别留下活口。”
蒙面人低声说道:“是!”然后转过身飞身上了房,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了。
院子里,更夫敲打着手上的梆子,心不在焉地在大院儿里蹓跶着。
此时楼上的客房内,高老爷子又吹了吹用青蒿编成的熏蚊子用的“火绳”,这才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。
尤掌柜的猜得不错,眼前这位名叫“高万祥”的老者,其实正是威震北中国武林的山西大侠,赫赫有名的“通背王”。老爷子之所以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,冒着被江湖朋友耻笑的风险,违心地把押运的“镖银”藏在棺材里,偷偷摸摸地走“暗镖”;完全是为了此一行的安全。自从外国的银行资本大量注入了中国,山西票号的生意就日趋没落。铁路的出现,彻底让靠长途贩运的山西商人,不得不无奈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一代武林豪杰,名震三晋的武林大侠高万祥老爷子,此前至少有将近二十年不走“镖”了,和绿林道儿上各路强梁们的交情也早就凉了。那些混不吝的土匪、强梁,如今谁还会买他——一个过了气的武师的面子?啥“通背王”?凭你再有工夫,还能斗得过西洋传来的枪子儿吗?当初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交过手哇!老祖宗传下来的“玩艺儿”,如今只能当玩艺儿了……
高万祥老爷子后悔了:真不该接这趟“镖”啊!眼下兵荒马乱的,当官的为了抢夺地盘儿,没完没了地打仗。正所谓“乱世英雄起四方”,社会一乱,老百姓的日子能好得了吗?听说现如今黑道儿上的土匪,连整列的火车都敢劫呀!万一有个闪失,我“大通镖局”的几世英名就算完啦!但愿老天爷保佑,让我们师徒这趟镖走得一路平安,顺顺当当地把“镖”押回太原……
渐渐地,老人闭上了眼睛,进入了梦乡。
鸡叫头遍了,院子里停放着的轿车内的两个人忙下了车,走到槽头,招呼喂牲口的伙计把他们的牲口牵出来,随后二人大声吆喝着牲口,笨手笨比较地套好了大车。这时,楼上的那几位也陆续赶了来,老当家的出面结清了店钱,此时正好鸡叫二遍。
老爷子吩咐伙计打开了大门,又招呼其他几个人上了那辆轿车,两挂大车便一前一后出了大门,沿着青石板铺成的大道,奔南驶去……
月亮已落下山了,小镇上黑乎乎、静悄悄的。马蹄踏在石板路上,发出的清脆声响。突然出现的马蹄声,惊得镇上的狗发出了阵阵狂吠。俄尔,还能听见住户儿家的孩子的哭闹声。待大车过后,小镇又恢复了宁静。
掌柜的尤鹏并没有看错,这两挂大车,可不是普通的运送灵柩回山西的运尸大车;而是山西“大通镖局”押运“黄货”的镖车。那黑漆棺材里装的也不是什么死人,而是大通镖局专门为山西“日升昌”票号从北京承运的八千两黄金。车上那位自称是“做药材生意的”长者,正是山西大通镖局的老掌门,江湖上赫赫有名的“通臂王”——老侠高万祥。
二十多年前,当时正值壮年的高万祥,凭着自己在山西武林中的地位,就已经不亲自出面替人押镖了。此一回高老爷子亲自出马,就足见这批货物的重要。而且,他们没有像以往押镖那样:亮出“镖旗”,喝着“镖号”上路。而是伪装成运灵柩还乡的,把黄金装进棺材中,悄没声儿地上了路。
这种“走镖”的形式,江湖上称之为“走暗镖”;是一种被人耻笑的行径。为保证这批黄金平安运回山西,老侠高万祥可以说是万分小心、搅尽脑汁了。
山西老侠,通臂王高万祥;声威曾经一度在江湖上是“如雷贯耳”。高家的大通镖局,早年更是名声远扬,无人不晓。要不然的话,老贼尤鹏怎么会也知道江湖上有“这么一号”呢?
高家祖上作过大清国的将军,参与过镇压河南的“白莲教起义”,那是受过皇封的。但后来获罪被贬,直到高万祥的父亲高金山当家时,高家才在山西挂起了“大通镖局”的牌子,凭着一身武艺,一刀一枪的真杀实砍,日久天长才逐渐在武林中创出了“通臂王”的美称。
大通镖局押的镖之所以在绿林道儿上畅通无阻,既得益于高家父子两代人的武艺出众,也得益于高家在绿林中广交朋友。绿林道儿上的人,只要到了山西,无不投奔设在太原的大通镖局。除了白吃、白住,临走还会得到一笔路费的资助。甚至有的人在山西翻船走水,入了大狱;也都找高家求助。高家在交朋友上花的钱,那可就“海”啦!正是这为朋友花出去的大把银钱,才换来了大通镖局在北中国诸省绿林道儿上的声威。高家父子铺就的“平安大道”,是拿银子堆起来的。
高万祥自小就随父亲练武,15岁便单独押镖上路了。大通镖局押的镖,那阵儿趟趟都是太平镖。相比老父亲来说,高万祥出名儿要早得多,但他却从未与认真的交过手,真的是“徒有其名”而已。
清末民初,满清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,向比利时政府借款修了京汉铁路。和过去商人们用骆驼、骡子、毛驴子运输货物相比,火车运输货物又快又经济又保险。铁路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:镖局的存在立即就受到了冷落,很快就纷纷关门歇业了。高万祥家的镖局也倒闭了,他给了伙计们一笔钱,遣散了镖局的武师。之后,高万祥便改行开设了武馆,凭借自己在武林中的名气,以收徒授业为生。
改号民国之后,北方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。这几个省虽有了铁路,但运输却很难畅通。山西的铁路修成了窄轨,与外界相通十分困难。还像过去那样靠原始的大车、骡马、骆驼运输货物吧,又惹不起沿途多如牛毛的土匪。于是,停业多年的镖局又纷纷重新开了业,历史好像又倒退了。
高万祥深知绿林道儿上的险恶,所以,他严守门户,执意不肯出山,为了不招灾惹祸,他甚至不许别人打着大通镖局的旗号去押镖。
山西的《日升昌》是我国最早出现的“票号”,它的存在的确曾经给经商的人们提供了诸多便利,高万祥的大通镖局几次受过《日升昌》票号的帮助,说起来两家也算是世交了。但日升昌毕竟是山西人开的买卖,处处显示出山西老西儿那种“舍命不舍财”的小家子气。人家外国人开的银行把业务的重点放在了投资实业上,将本逐利,很快就赚了大钱。而日升昌的当家人只知道抠抠唆唆地穷算计,却不敢大把大把地往实业上投资;所以日升昌的买卖很快就开不下去了。无奈,日升昌只得关闭了设在外地的分号,把资本往山西省内回拢。
然而,如何把设在北京分号的这笔巨款带回山西,就成了掌柜的一块心病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把北京分号的资产兑换成了八千两黄金。和别的货币相比,黄金一是最便于携带;二是最为稳定和通用。可怎么把这一大笔黄金运回山西呢?思前想后,老掌柜只好亲自出面到太原来求高万祥,求他无论如何辛苦一趟。敢走这条道儿的,现如今恐怕也只有高万祥了。
几代世交,高万祥实在担不起人家那个“求”字。他只得硬着头皮勉强答应了下来,然后便带上一应手续和七个得力的徒弟,到北京来押这趟镖。
十多年不趟“绿林道儿”了,自改行开武馆以来,高万祥和道儿上的朋友也都断了来往。虽然高家的大通镖局在江湖上曾经是一块畅通无阻的金字招牌,但事隔多年,高万祥对绿林中的变化可以说一无所知。思虑再三,他决定把黄金装入棺材中,他们师徒众人扮成运灵柩回乡的人,用“走暗镖”的方法,将那批黄金运回。
在绿林道儿上,走“暗镖”是要遭人耻笑的。一般说来,除了押运“犯禁”的货物,镖师们都不愿意走暗镖。对于走暗镖的“趟子”,绿林道儿上的强梁们从来不客气,撞上便是一场拼杀,根本就不会看什么人的面子,跟什么人讲交情。
尽管如此,高万祥还是决定:此次进京押运这批黄金,要走暗镖。他早已过了那“强出头”的年纪,为了稳妥,低个头又有何妨?
出了沿河镇,地面上就是土路了;由于道路坑洼不平,大车颠簸的程度加剧了。东方天际渐呈一抹鱼肚白,三星渐渐暗了下去。
高万祥嫌车内太挤,就下了车,伸了伸腰腿,然后跟在大车后边,边走边哼起了山西梆子。几个徒弟也下了车,跟在师傅后边,好奇地问这、问那。
高万祥此次带来的七个徒弟,都是头一次出远门儿,因此个个都显得很兴奋。其中一个问道:“师傅,前边是啥地方?”
高万祥微微一笑,说道:“前边……,再走就到良乡县县城了。这一带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的俗话:‘精涿州、怯良乡,不开眼的房山县’。”
徒弟们立刻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七嘴八舌地吵吵着:“啥意思嘛?”
高万祥“呵呵”一笑,随后就打开了“话匣子”,滔滔不绝地说开了:“咱先说这涿州,嘿!那儿自古就是个出好汉的地界儿,三国时的刘、关、张桃园儿结义,就发生在涿州。那刘备和张飞都是涿州的人,他们可给涿州的老百姓长了脸了。相传宋太祖赵匡胤的老家也是涿州的,我说,这二位可都当了皇上;你们说涿州这地界儿是不是好风水?除去风水好,涿县地处北京城通向中原各省的大道上,这儿的人眼界子宽,见识广;所以都特别的精明。但凡和涿州人打过交道的人,都很佩服涿州人的精明,这就有了‘精涿州’的说法。”
大伙儿全笑了。
高老爷子接着又说道:“咱再说这良乡县,老的良乡县城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,每个城门都有瓮城,北门、东门、南门的瓮城城门都是顺时针方向设计的,按照这个规律,西门的瓮城应该面向北,这样才能让整个儿城市的建筑布局,构成‘万字不到头’图案的统一布局。但是,西门的瓮城却建成面向南了,就成了逆时钟方向设计;这样一来,整个儿县城的四个城门的设计就“怯”了。由于县城的城门修得不规矩,因此良乡县就被人称为了‘怯良乡’了……”
徒弟们的笑声打断了老爷子的讲述,一个徒弟又问道:“您刚才还说房山县咋地啦?”
高老爷子沉吟了一会,接着说道:“从北京城出来一直奔南走,过了良乡县后,就进入了房山县境内了。相传清朝的时候,一次乾隆皇帝到河北省易县泰宁山下的西陵祭奠先父(雍正皇帝)。路过房山城时,当时的知县姓杨,为人正直,从不拍皇上的马屁。他听说乾隆皇帝祭祖要路过本县,估计皇上既是来此祭奠先人,大概就不会在半路上多耽搁,他就在城门前摆了桌清茶,简单地迎送一下。乾隆皇帝那天凑巧走到这儿的时候,真的也饿了。见接驾的下属没有预备饭,心里就很不痛快。但当着文武百官又不好意思说什么。过了房山城便对大臣和珅说道:“这个杨知县可真小气,连顿饭都没让朕吃上,真是不开宴的房山县呀!”那和珅也对这杨知县不摆宴席接驾耿耿于怀,听皇上这么一说,连声重复了好几遍“不开宴的房山县”,说着说着便有意说走了音,说成了“不开眼的房山县”,意在发泄对那位杨知县的不满。接着他又把这句话说给了几位随行的大臣,他们一听,也说那杨知县太小气,不久这句话就传开了。从此,房山县就落了个“不开眼”的外号;其实应该说是“不开宴”的意思。
“那……,咱们今天是不是也不打算在房山县境内吃饭,也赶到涿州去落脚?”
高万祥点了点头,压低了声音说:“天刚擦黑儿时,道儿上劫道的最多。咱们早点儿上路,趁天黑前就赶到涿州了;今晚上咱就歇在涿县县城。待会儿,咱们赶到良乡县县城,在那儿吃早饭。然后再买点烧饼、牛肉,带在路上吃,晌午饭就这么凑合啦。晚上赶到涿州,再正经吃晚饭。既然人家房山县有‘不开宴’的习惯,咱也只好入乡随俗,不在那儿吃午饭了。”徒弟们听了这话,又是一阵大笑。
说话间,师徒八人来到了一座小山丘下。那山丘看上去并不高,但正伫立在官道旁,山丘上长满了半人高的酸枣棵子,微风吹来,黑乎乎的酸枣棵子轻轻涌动着,立刻引起了高万祥的警觉,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正疑惑间,山岗上响起了一阵拉动枪栓的声响,随即传出一声东北口音沙哑嗓音的呐喊:“站住!不站住老子开枪啦——”
对方在高处,高万祥师徒在低处;人家在暗处,他们师徒八人在明处;情况对高万祥师徒极为不利。几个徒弟当下便亮出了随身携带的短兵器,拉开了格斗的架式。
高万祥一惊,忙示意徒弟们“不可造次”,他则故意“哈哈”地笑着,高扬起两只手,示意自己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,迎着前边儿酸枣棵子中传来的吼叫声,忙挺身向前,施了个“江湖礼”,双手抱拳,高声问道:“是哪路朋友,难道连送‘死人’的也不放过吗?”
“妈拉个巴子的,谁要棺材里的死人?老子要后边车里的小娘们儿!哈……”
高万祥心里一惊,不由得暗暗叫苦。当初,他考虑到此去山西一千多里地,徒步行走太辛苦,这才买下了两辆大车,一挂带篷顶的轿车,为的是师徒们走累了轮流着上车歇歇脚。另一辆平板大车,拉的是一口棺材。没想到,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。劫道的土匪认定那挂坐人的“轿车”内一定坐着死者的女眷。看来这是一伙劫财又劫色的土匪,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高老侠眼珠儿一转,紧跟着双手一抱拳,接着大声说:“这位朋友真会说笑话,我们山西人外出做买卖从来不带眷属,几位应当有个‘耳闻’吧?我们是专做药材生意的,我是掌柜的,死了的是我的账房先生……”
“少跟老子扯这些没用的,今天碰上我,算他妈你倒霉。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祭日,弟兄们,下家伙!”话音一落,山丘上顿时枪声大作。高万祥一看不妙,忙向前一蹿,然后来了个就地十八滚,便滚进了路旁的高粱地中。他想要站起身来,但左腿一阵剧痛,高万祥一下子便疼得昏了过去。
文丨梁亚明
下一章:风雨沿河镇第2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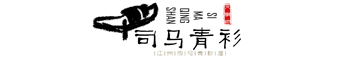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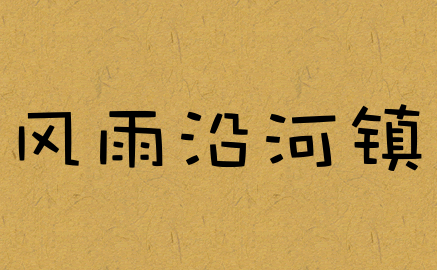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